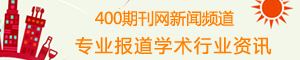版画鲁迅像,汪刃锋1956年作 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作为一位在现当代文学领域至关重要的大家,他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研究阐释空间,导致关于他的研究至今是一门显学。然而另一方面,其丰富性也对今天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天的鲁迅研究存在怎样的误区?如何更好地继承鲁迅的精神遗产,使之与时代激荡出更加广泛的共鸣?本报记者对话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彬彬。
嘉宾:王彬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采访:邵岭本报首席记者
记者:对当下海内外鲁迅研究的总体判断是怎样?你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研究鲁迅,需要自己有充分的知识和文化储备。据你观察,当下在鲁迅研究领域,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重要的误区?
王彬彬:鲁迅是现代作家里被研究最多的。一方面,研究鲁迅很容易,因为资料很多,而且鲁迅又是个极其丰富的对象。研究对象如果很单纯,意义很明确,就没有太多可以阐释的空间。而鲁迅的文本和整个人生经历都是内涵丰富,有很多不确定性,就给研究留下了很多阐释的可能性。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狂人日记》就可以有很多种阐释。鲁迅到底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到目前为止都不确定,不像有的作家有的小说,大家对他们的判断认识和审美评价都是定型了的。鲁迅所有文本都是这样,因为他的表达方式,语言特性,和思想的复杂性,都是可以从各种角度阐释的。
但实际上,鲁迅研究很难,我经常跟学生讲,轻易不要写研究鲁迅的文章,一是鲁迅这个对象本身理解起来不容易,二是很多话别人说过了,今天再要对鲁迅的思想状况和文学特色有一些有新意的有价值的看法,很难,对研究者要求很高,需要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很好的语言感觉,很充分的常识和对现代文化史政治史的充分了解。如果基本常识都没有,而是把已有的东西做重新组装,或者用时髦理论附会,那就没有意义。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多,这不是很负责的研究方式。
记者:关于基本常识的缺乏,能举例子吗?什么样的基本常识,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是缺乏的?
王彬彬:比如有人写文章说,鲁迅在广州洗澡多,是为了讨好许广平。有没有基本常识?洗澡多是因为广州热嘛!广州是他所有生活过的地方里气候最热的。他日记里记载,六七月份的时候3天才洗1次,已经很少了。还说鲁迅在中山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是早就预见到了2007年教育部下文,教授要给本科生上课。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山大学刚刚创办,本科就是它最高级别的学生了。连这种常识都没有还研究鲁迅?
另外,鲁迅的文本意义是很丰富的,一篇短文也有多层意思。但有些研究者,连鲁迅文本最表层的意思都没有弄懂。鲁迅有一篇文章叫《导师》,告诫青年人要主动去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要相信“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这里的“鸟导师”指的不是学校的老师,而是权威名流,精神上的引导者。但就有人写文章说鲁迅后来离开了学校,“不当鸟导师了”。这就是根本没有读懂鲁迅。
记者:是什么造成了鲁迅的丰富?
王彬彬:两个原因。
一个是鲁迅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们说,越是好的文学语言越有暗示性。古代诗人里,白居易为什么比不上李商隐?因为他语言直白,暗示性比较少,往往只有一个意思。而鲁迅是个语言大师,语言感觉非常好,他的遣词造句是有巨大包容性暗示性和多层次性的。
还有就是他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写文学作品不是把一个事情想明白了再写,如果想明白了就没必要写小说了,去写论文就好了。有时恰恰对生活对社会有某种困惑和迷茫,就是为了表达这样的困惑和迷茫,这才是一个好的作家。鲁迅的好多小说都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可供阐释的空间。一般文本都有表层故事,如果表层故事都读不懂而要研究鲁迅,那不是胡扯吗?
记者: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资料被发现,新一代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些质疑鲁迅的观点,特别是他对日本的态度。证据之一就是他的日记里没有记录和日本有关的大事。你怎么看?
王彬彬:“九·一八”以后,鲁迅当然写过相关的文章。《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不都是在说抗日问题吗?批评当时一些年轻人的草率轻薄的言行,说这样是不行的。黑龙江的马占山抵抗日本,上海热血青年组成“青年援马团”,宣称要步行去东北,而且只穿一件夹袄。鲁迅就说了,现在有铁路,为何要走着去?东北很冷,为何不多带点衣物?鲁迅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做戏。结果被鲁迅说中,他们在常州玩了一圈就回上海了。
鲁迅对于中日关系是有自己一整套看法的,他对双方都很了解,而这种看法,几句话是说不清的。但是他说过一句非常有价值的话:什么时候中日之间能够真正和平?只有中国力量和日本力量真正对等的时候。这句话是很有力量的。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而这是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的。
至于鲁迅的日记,鲁迅日记的特色就是从来不记国家大事。他的日记都是琐事,收到谁的钱,还了谁的钱,跟谁一起吃饭,买了几本书。这是他写日记的原则,不对大事发表意见。他觉得,日记没有必要记大事,大事都在报纸上了,日记是记私事备查的,不记会忘。他的日记主要功能是备查。比如借钱。是备忘录。鲁迅在北京时期是经常借钱的。到上海就不需要借了。
我20年前就关注过这个问题。一一对照过。后来我发现他就是这么个人。包括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大事,也一笔带过,包括与周作人,闹那么大的事,也就“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就完了。
记者:这个有点像红学研究。研究到现在,要有新发现新观点新角度很难,为了做出成果,只能不走寻常路。
王彬彬:对。一方面,关于鲁迅的阐释已经很多,要有新意不容易,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不仅仅是发现新史料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主体跟研究对象的碰撞,在这样一种碰撞中产生出新理解。这里面,对研究主体要求很高,有没有资格能力与鲁迅产生碰撞,这很重要。你面对这样一个对象,不能老是抓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但是今天有人就是这么做,这是一种学术生产,也没什么奇怪。因为鲁迅的资料太多,随便搞一下就是一篇文章。
记者:很多青年学者还是对鲁迅很有兴趣,经常会引用鲁迅的语录。你自己也带了很多学生,也接触很多青年学者。你对于他们研究鲁迅有什么建议吗?
王彬彬:鲁迅研究,我一直认为,对研究者的要求蛮高的。要研究鲁迅,首先要清楚鲁迅是不是一个适合你研究的对象。比如你自己首先要是一个语言感觉很好的人,不然你不可能真正去欣赏鲁迅。因为你感觉不到他语言中的内涵。还有就是鲁迅研究领域已经被弄得很乱,很多史料都是有问题的,要经过各种考辨,不能拿来就用。现在你要写一篇骂鲁迅的文章很容易,一大堆文章;要写一篇歌颂的也很容易,一大堆资料。但很多的回忆、说法都是靠不住的。要进入这个领域,对于大的状况要有了解,要知道对于资料的运用要特别小心。
研究鲁迅,首先应该尽可能地直接面对鲁迅文本。我们首先应该明确,鲁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忽视了这一点,不对他文本的丰富性有深入的体味,就在外围的一大堆堆积如山的史料里东找一点西找一点,很容易,但也很扯淡。
而且我反对一个人只研究鲁迅,或者只研究一个作家,一个问题。这样一定研究不好鲁迅。当然你可以在一些史料问题上做得很深,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做得很好,但是视野会狭窄。
记者:有些研究者过多倚重史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从文学层面上认识鲁迅,还是面对文本更难?
王彬彬:很多人不觉得鲁迅好。他们没有从鲁迅作品中获得一种巨大的审美愉悦和陶醉,那说明他的能力在面对鲁迅时就有一个审美盲区。
记者:从事鲁迅研究这么多年,你本人最喜欢鲁迅的哪部作品?
王彬彬:我个人很早读鲁迅就被鲁迅吸引,但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很多时候我不是把他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欣赏对象,什么时候拿起他的作品,哪怕已经读过无数遍,都觉得深刻准确有味道,那么美。在阅读之余有些想法,写些东西,如此而已。
这种吸引首先是语言,那种表达方式。小时候读《野草》散文集中《秋夜》的第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有一种奇异的美。
记者:你曾经写过一篇《月夜里的鲁迅》,里面提到说,很多人认为鲁迅是严酷的,但其实不仅仅如此。你怎么会关注到这一点?
王彬彬:就是从文本出发。鲁迅研究的史料太多,而我的文章引用别人的资料是比较少的,都是直接面对文本,而不是从史料里去发现。你对鲁迅文本的感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张三李四怎么说。关键是你自己怎么说。
这就是我从他的日记里发现的问题。他在北京的日记里经常会记到月亮,这个很独特。很少有人日记里经常写月亮。我发现这个和鲁迅的精神有关系,再对照他同期写作里的内容,《狂人日记》《秋夜》里写到月亮,你再看他当天日记里关于月亮的描写,坐在窗前,窗外正有一轮月亮,这其中一定是有关系的。然后你会发现鲁迅精神上温热的伤感的无奈的软弱的一面,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鲁迅。其实他的很多文本表达的正是伤感和无奈。这是我直接面对文本产生的感受。
记者:我突然想到,做现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到后来拼的就是视角,因为大家能接触到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关键是你能用什么新的眼光去看待材料。
王彬彬:视角就是感受,你一定要有独特的感受,才能有独特的视角。这就是你对研究对象的直接感受,抛开所有史料。很多人一辈子研究鲁迅,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和鲁迅零距离接触过,而是通过各种史料各种中介来认识鲁迅。你的生命从来没有和鲁迅的生命直接碰撞过,怎么可能读得懂鲁迅?鲁迅对于他们,完全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记者:我们刚才在讨论鲁迅时一直没有提胡适,你会觉得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吗?
王彬彬:很多人会把他们进行比较,因为两个人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巨大的存在。但非此即彼的选择绝对是荒谬的。他们两人完全是可以并存互补的,他们的对立性没有通常以为的那么大。特别是在文化理念上,他们几乎没有对立。胡适也是终身坚持启蒙立场,坚持对旧文化的批判。这和鲁迅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胡适的气质背景不一样,所以除了思想启蒙之外,胡适还关注制度层面的建设,而鲁迅对这方面是没有兴趣的。当然两人的生活境遇差别也非常大,胡适当了北大教授,得意风光。“九·一八”前后,他就可以和朋友一起,夏天去北戴河消暑度假,这在鲁迅是不可想象的。鲁迅经常用一个词就是“挣扎”。生活就是苦苦挣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两个人都是巨大的文化存在,对于我们后人来讲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记者:怎么看待鲁迅作品被撤出中学教材?是鲁迅过时了吗?鲁迅以及鲁迅研究,对当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今天为止仍然非常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王彬彬:首先我也并不认为中学生课文里应该选很多鲁迅作品,因为鲁迅的很多东西不适合中学生来学,中学生理解起来是很难的。如果给中学生读,要选那些文学性特别好的,比较温暖浅显,简短凝练的。但过去我们选择的标准不是这样,会有文学以外的标准和考量。
另外,我们的课堂上对鲁迅作品的阐释和解读也有问题。比如《孔乙己》,老师就会说,是批判科举制度,但这只是鲁迅小说最表层的意思。这样解释就把鲁迅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肤浅化了。
其实这些问题在技术上操作不难,但牵涉到很多大的文化背景,其实可以好好讨论,请专家来讨论,选文和解读。
鲁迅当然没有过时。他在中国现代史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一方面,他是整个中国从旧文化向新文化转变,从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么一位身上凝聚了巨大历史内涵和时代内涵的人物;另一方面,鲁迅的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小说写作在他那个时代都是一流的,比如鲁迅对中国文学史的看法,就《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么一篇文章,对于魏晋文学的看法,今天所有古代文学史家都不敢绕过他。
然而,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鲁迅,其意义远远没有被认识。我们过去总是不把鲁迅作为文学家,而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鲁迅,其价值是被低估的,还没有被认识得很充分。他的作品里巨大的文学性,他用现代汉语进行文学表达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比如他的语言艺术,用现代汉语进行文学表达的才华,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正如有人指出的,《狂人日记》里一句“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就写出了一个精神病人的状态。一个平庸的作家,写了3000字,还写不出这个状态。
今天的鲁迅研究存在怎样的误区?如何更好地继承鲁迅的精神遗产,使之与时代激荡出更加广泛的共鸣?本报记者对话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彬彬。
嘉宾:王彬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采访:邵岭本报首席记者
记者:对当下海内外鲁迅研究的总体判断是怎样?你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研究鲁迅,需要自己有充分的知识和文化储备。据你观察,当下在鲁迅研究领域,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重要的误区?
王彬彬:鲁迅是现代作家里被研究最多的。一方面,研究鲁迅很容易,因为资料很多,而且鲁迅又是个极其丰富的对象。研究对象如果很单纯,意义很明确,就没有太多可以阐释的空间。而鲁迅的文本和整个人生经历都是内涵丰富,有很多不确定性,就给研究留下了很多阐释的可能性。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狂人日记》就可以有很多种阐释。鲁迅到底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到目前为止都不确定,不像有的作家有的小说,大家对他们的判断认识和审美评价都是定型了的。鲁迅所有文本都是这样,因为他的表达方式,语言特性,和思想的复杂性,都是可以从各种角度阐释的。
但实际上,鲁迅研究很难,我经常跟学生讲,轻易不要写研究鲁迅的文章,一是鲁迅这个对象本身理解起来不容易,二是很多话别人说过了,今天再要对鲁迅的思想状况和文学特色有一些有新意的有价值的看法,很难,对研究者要求很高,需要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很好的语言感觉,很充分的常识和对现代文化史政治史的充分了解。如果基本常识都没有,而是把已有的东西做重新组装,或者用时髦理论附会,那就没有意义。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多,这不是很负责的研究方式。
记者:关于基本常识的缺乏,能举例子吗?什么样的基本常识,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是缺乏的?
王彬彬:比如有人写文章说,鲁迅在广州洗澡多,是为了讨好许广平。有没有基本常识?洗澡多是因为广州热嘛!广州是他所有生活过的地方里气候最热的。他日记里记载,六七月份的时候3天才洗1次,已经很少了。还说鲁迅在中山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是早就预见到了2007年教育部下文,教授要给本科生上课。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山大学刚刚创办,本科就是它最高级别的学生了。连这种常识都没有还研究鲁迅?
另外,鲁迅的文本意义是很丰富的,一篇短文也有多层意思。但有些研究者,连鲁迅文本最表层的意思都没有弄懂。鲁迅有一篇文章叫《导师》,告诫青年人要主动去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要相信“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这里的“鸟导师”指的不是学校的老师,而是权威名流,精神上的引导者。但就有人写文章说鲁迅后来离开了学校,“不当鸟导师了”。这就是根本没有读懂鲁迅。
记者:是什么造成了鲁迅的丰富?
王彬彬:两个原因。
一个是鲁迅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们说,越是好的文学语言越有暗示性。古代诗人里,白居易为什么比不上李商隐?因为他语言直白,暗示性比较少,往往只有一个意思。而鲁迅是个语言大师,语言感觉非常好,他的遣词造句是有巨大包容性暗示性和多层次性的。
还有就是他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写文学作品不是把一个事情想明白了再写,如果想明白了就没必要写小说了,去写论文就好了。有时恰恰对生活对社会有某种困惑和迷茫,就是为了表达这样的困惑和迷茫,这才是一个好的作家。鲁迅的好多小说都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可供阐释的空间。一般文本都有表层故事,如果表层故事都读不懂而要研究鲁迅,那不是胡扯吗?
记者: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资料被发现,新一代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些质疑鲁迅的观点,特别是他对日本的态度。证据之一就是他的日记里没有记录和日本有关的大事。你怎么看?
王彬彬:“九·一八”以后,鲁迅当然写过相关的文章。《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不都是在说抗日问题吗?批评当时一些年轻人的草率轻薄的言行,说这样是不行的。黑龙江的马占山抵抗日本,上海热血青年组成“青年援马团”,宣称要步行去东北,而且只穿一件夹袄。鲁迅就说了,现在有铁路,为何要走着去?东北很冷,为何不多带点衣物?鲁迅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做戏。结果被鲁迅说中,他们在常州玩了一圈就回上海了。
鲁迅对于中日关系是有自己一整套看法的,他对双方都很了解,而这种看法,几句话是说不清的。但是他说过一句非常有价值的话:什么时候中日之间能够真正和平?只有中国力量和日本力量真正对等的时候。这句话是很有力量的。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而这是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的。
至于鲁迅的日记,鲁迅日记的特色就是从来不记国家大事。他的日记都是琐事,收到谁的钱,还了谁的钱,跟谁一起吃饭,买了几本书。这是他写日记的原则,不对大事发表意见。他觉得,日记没有必要记大事,大事都在报纸上了,日记是记私事备查的,不记会忘。他的日记主要功能是备查。比如借钱。是备忘录。鲁迅在北京时期是经常借钱的。到上海就不需要借了。
我20年前就关注过这个问题。一一对照过。后来我发现他就是这么个人。包括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大事,也一笔带过,包括与周作人,闹那么大的事,也就“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就完了。
记者:这个有点像红学研究。研究到现在,要有新发现新观点新角度很难,为了做出成果,只能不走寻常路。
王彬彬:对。一方面,关于鲁迅的阐释已经很多,要有新意不容易,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不仅仅是发现新史料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主体跟研究对象的碰撞,在这样一种碰撞中产生出新理解。这里面,对研究主体要求很高,有没有资格能力与鲁迅产生碰撞,这很重要。你面对这样一个对象,不能老是抓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但是今天有人就是这么做,这是一种学术生产,也没什么奇怪。因为鲁迅的资料太多,随便搞一下就是一篇文章。
记者:很多青年学者还是对鲁迅很有兴趣,经常会引用鲁迅的语录。你自己也带了很多学生,也接触很多青年学者。你对于他们研究鲁迅有什么建议吗?
王彬彬:鲁迅研究,我一直认为,对研究者的要求蛮高的。要研究鲁迅,首先要清楚鲁迅是不是一个适合你研究的对象。比如你自己首先要是一个语言感觉很好的人,不然你不可能真正去欣赏鲁迅。因为你感觉不到他语言中的内涵。还有就是鲁迅研究领域已经被弄得很乱,很多史料都是有问题的,要经过各种考辨,不能拿来就用。现在你要写一篇骂鲁迅的文章很容易,一大堆文章;要写一篇歌颂的也很容易,一大堆资料。但很多的回忆、说法都是靠不住的。要进入这个领域,对于大的状况要有了解,要知道对于资料的运用要特别小心。
研究鲁迅,首先应该尽可能地直接面对鲁迅文本。我们首先应该明确,鲁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忽视了这一点,不对他文本的丰富性有深入的体味,就在外围的一大堆堆积如山的史料里东找一点西找一点,很容易,但也很扯淡。
而且我反对一个人只研究鲁迅,或者只研究一个作家,一个问题。这样一定研究不好鲁迅。当然你可以在一些史料问题上做得很深,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做得很好,但是视野会狭窄。
记者:有些研究者过多倚重史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从文学层面上认识鲁迅,还是面对文本更难?
王彬彬:很多人不觉得鲁迅好。他们没有从鲁迅作品中获得一种巨大的审美愉悦和陶醉,那说明他的能力在面对鲁迅时就有一个审美盲区。
记者:从事鲁迅研究这么多年,你本人最喜欢鲁迅的哪部作品?
王彬彬:我个人很早读鲁迅就被鲁迅吸引,但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很多时候我不是把他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欣赏对象,什么时候拿起他的作品,哪怕已经读过无数遍,都觉得深刻准确有味道,那么美。在阅读之余有些想法,写些东西,如此而已。
这种吸引首先是语言,那种表达方式。小时候读《野草》散文集中《秋夜》的第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有一种奇异的美。
记者:你曾经写过一篇《月夜里的鲁迅》,里面提到说,很多人认为鲁迅是严酷的,但其实不仅仅如此。你怎么会关注到这一点?
王彬彬:就是从文本出发。鲁迅研究的史料太多,而我的文章引用别人的资料是比较少的,都是直接面对文本,而不是从史料里去发现。你对鲁迅文本的感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张三李四怎么说。关键是你自己怎么说。
这就是我从他的日记里发现的问题。他在北京的日记里经常会记到月亮,这个很独特。很少有人日记里经常写月亮。我发现这个和鲁迅的精神有关系,再对照他同期写作里的内容,《狂人日记》《秋夜》里写到月亮,你再看他当天日记里关于月亮的描写,坐在窗前,窗外正有一轮月亮,这其中一定是有关系的。然后你会发现鲁迅精神上温热的伤感的无奈的软弱的一面,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鲁迅。其实他的很多文本表达的正是伤感和无奈。这是我直接面对文本产生的感受。
记者:我突然想到,做现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到后来拼的就是视角,因为大家能接触到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关键是你能用什么新的眼光去看待材料。
王彬彬:视角就是感受,你一定要有独特的感受,才能有独特的视角。这就是你对研究对象的直接感受,抛开所有史料。很多人一辈子研究鲁迅,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和鲁迅零距离接触过,而是通过各种史料各种中介来认识鲁迅。你的生命从来没有和鲁迅的生命直接碰撞过,怎么可能读得懂鲁迅?鲁迅对于他们,完全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记者:我们刚才在讨论鲁迅时一直没有提胡适,你会觉得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吗?
王彬彬:很多人会把他们进行比较,因为两个人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巨大的存在。但非此即彼的选择绝对是荒谬的。他们两人完全是可以并存互补的,他们的对立性没有通常以为的那么大。特别是在文化理念上,他们几乎没有对立。胡适也是终身坚持启蒙立场,坚持对旧文化的批判。这和鲁迅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胡适的气质背景不一样,所以除了思想启蒙之外,胡适还关注制度层面的建设,而鲁迅对这方面是没有兴趣的。当然两人的生活境遇差别也非常大,胡适当了北大教授,得意风光。“九·一八”前后,他就可以和朋友一起,夏天去北戴河消暑度假,这在鲁迅是不可想象的。鲁迅经常用一个词就是“挣扎”。生活就是苦苦挣扎。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两个人都是巨大的文化存在,对于我们后人来讲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记者:怎么看待鲁迅作品被撤出中学教材?是鲁迅过时了吗?鲁迅以及鲁迅研究,对当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今天为止仍然非常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王彬彬:首先我也并不认为中学生课文里应该选很多鲁迅作品,因为鲁迅的很多东西不适合中学生来学,中学生理解起来是很难的。如果给中学生读,要选那些文学性特别好的,比较温暖浅显,简短凝练的。但过去我们选择的标准不是这样,会有文学以外的标准和考量。
另外,我们的课堂上对鲁迅作品的阐释和解读也有问题。比如《孔乙己》,老师就会说,是批判科举制度,但这只是鲁迅小说最表层的意思。这样解释就把鲁迅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肤浅化了。
其实这些问题在技术上操作不难,但牵涉到很多大的文化背景,其实可以好好讨论,请专家来讨论,选文和解读。
鲁迅当然没有过时。他在中国现代史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一方面,他是整个中国从旧文化向新文化转变,从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么一位身上凝聚了巨大历史内涵和时代内涵的人物;另一方面,鲁迅的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小说写作在他那个时代都是一流的,比如鲁迅对中国文学史的看法,就《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么一篇文章,对于魏晋文学的看法,今天所有古代文学史家都不敢绕过他。
然而,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鲁迅,其意义远远没有被认识。我们过去总是不把鲁迅作为文学家,而作为一个文学家的鲁迅,其价值是被低估的,还没有被认识得很充分。他的作品里巨大的文学性,他用现代汉语进行文学表达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比如他的语言艺术,用现代汉语进行文学表达的才华,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正如有人指出的,《狂人日记》里一句“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就写出了一个精神病人的状态。一个平庸的作家,写了3000字,还写不出这个状态。
[ 编辑: 何雯 ]